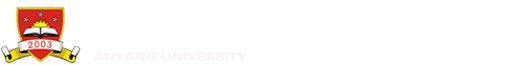学术争鸣|陈凡 李嘉伟:工匠精神价值维度的阐释与弘扬
摘 要 [摘要]工匠精神是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凝结和彰显的精神品格,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鲜明的时代特色。阐释工匠精神的价值维度可从个体、群体以及人类整体三方面展开:从个体层面看,起源于手工时代的工匠精神彰显了个体工匠在制作过程中求新、求精、求道的价值追求;从群体层面看,工匠精神作为工匠共同体的智慧结晶以职业伦理的形式得以延续,塑造了工匠群体的价值规范;从人类整体层面看,当机器取代人类成为制造活动的主体时,由于标准化量产的背后暗含着同质化危机,重塑工匠精神必须捍卫人类主体价值。弘扬工匠精神的价值维度,一要促进人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自我完善;二要以技术的生活本质为基点,促使人在面对技术的包围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特性,避免被技术同质化;三要在未来智能制造的过程中体现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气质,恢复和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进而实现人与技术的共在共生。 [关键词]工匠精神;个体品质;职业伦理;人类命运;价值维度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灿烂的技术成就和历史悠久的工匠传承,工匠精神即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凝结和彰显的精神品格。从技术发展史的维度看,依据制造方式的不同,可以将人类历史分为手工制造时代、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以及智能制造时代三个阶段,由于技术特点的不同,工匠精神在每个时代的内涵表征也有所不同。发源于手工业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以技能为核心,体现了个体劳动者的工作能力、价值追求和人生境界;工业化时代的工匠精神由单一技能的熟练转变为与机器生产相契合的能力,表现为工人自我约束的职业伦理规范;智能化时代的工匠精神面对同质化危机的挑战,对其内涵与价值的理解应超越个体品质和职业伦理的维度,表现为在技术时代捍卫人类主体性,这不仅仅是强调制造过程中人的核心地位,更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命运。 因此,工匠精神并非一成不变,今天我们对工匠精神的理解,需要与当前时代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劳动者素质的逐步提高,人们对工匠精神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将工匠精神的内涵高度概括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①,并多次指出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能水平,以适应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可见,工匠精神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②、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工匠精神价值内涵在个体、群体以及人类整体三个方面的演变与阐释,新时代弘扬工匠精神,应当重视其在生产、生活以及生存层面的特殊价值。
一、工匠精神彰显个体价值追求 工匠在一般意义上指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劳动者,工匠精神简言之就是在具体实践中为了把事情做好而理应具备的精益求精的态度与素质。工匠精神自古有之,其内涵同古代工匠的劳动息息相关,在中西方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工匠一词在英语中的表述一般为craftsman,德语为handwerker,法语为artisanal。西方语境下,人们对工匠的定义与手工劳动密切相关,德语用handwerk(手工)指涉匠人的劳动,法语则是artisana(l手艺),英语中的craft含义则较为广泛,其最初表达的是力量,之后演变出技能、贸易、建造等含义,例如国家管理又称statecraft。③中文语境下,“工匠”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马蹄篇》——“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④。《说文解字》中记载:“工,巧饰也”,“巧,技也”,“饰,㕞也”。⑤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提到:“凡物去其尘垢,即所以增其光彩,故㕞者,饰之本意。”⑥因此,工的含义即通过技能使物增光添彩,其核心在于技能的掌握与运用。匠字由“匚”与“斤”会意而成,“匚”指方形盛物的器具,“斤”则指砍斫木头的小斧,其字形为斧头装在筐中,故《说文解字》中对匠的解释为“匠,木工也”,王筠在《说文解字释例》中提到“乃以箱箧盛器械者,必系工人”①。与“工”相比,“匠”专指木工,其内涵更为具体,但外延不如“工”所表达的丰富。②综上,通过词源学的考察可以发现,技能是工匠之所以成为工匠的核心,是工匠存在的基础,作为工匠活动表征的工匠精神亦是以技能为核心展开的。 首先,早期工匠对技能的掌握并不仅仅表现在学会了相应的操作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创造性思维的本质。在文明的开端,掌握先进技艺的工匠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发明,解决人们在生存与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并由此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例如《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③希腊神话中作为工匠之神的赫菲斯托斯则是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与其他身形俊美的神不同,赫菲斯托斯相貌丑陋且跛足,但其心灵手巧,技艺非凡,且为人类传授匠艺,为人类带来和平,故受到人们的推崇。工匠通过掌握技能而成为人类社会的技术主体,在社会发展的早期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考工记》记载,百工是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妇功并列的国家“六职”之一,其职责为“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④,包括制造器物的专业工匠、技艺指导者以及行政官员。古希腊荷马时代表达匠人的词汇demioer-gos,由demios(公共的)和ergon(生产性的)复合而成,工匠发明创造工具,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也是为了使这些工具用于公共领域,从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类居有定所。此时的匠人在社会中处于中等阶层,位于贵族与奴隶之间,其指称的范围不仅包括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还包括医生、信使以及基层官员等职业。⑤从人类学的角度看,由工具的使用者向工具的制造者转变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有着重要意义,早期工匠也因其所具有的发明创造能力而获得民众的爱戴,成为某一行业的祖师。 其次,在前人基础上对技能的精益求精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造物理念与价值追求。《考工记》中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⑥,意为智慧且富有创造才能的人创制器物,技艺高超的人传承和改良制作方法并不断创新,以此为职业世代相传,即为工匠,百工制作的各类器物,都是圣人的发明创造。工匠的职责在于将圣人的造物技能记载和传承下来,但是对前人技能的模仿并不能为工匠带来满足感,工匠的骄傲源于自身技能的不断精进和对产品品质的不懈追求。考古研究表明,青铜铸造技术在夏代就已出现,在商代进入全盛时期。古代青铜器铸造主要用于制作礼器和兵器,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组别、数量最多、音律最全、气势最为雄伟的一套编钟,其上刻有关于先秦时期乐律学知识的铭文3775字,且无论是大钟还是小钟,均可同时或分别击发出两个乐音,其音域达五个半八度,中间三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音乐性能相当完备。这表明当时的工匠在铸造技术上具备声学设计工艺,可根据钟体的结构、长度以及合金成分的比例把握编钟的声学要素。此外,同时期出土的其他青铜文物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匠在铸造技术方面已掌握双面范铸、分范合铸以及失蜡铸造等技术,其中失蜡铸造同现代熔模铸造极为相似,为世界铸造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见,古代中国辉煌灿烂的技术成就与工匠精巧绝伦的技艺密切相关。同时工匠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也为当时人们所称赞,《诗经》中“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①,即以治器方法形容君子研究学问和陶冶品行的精益求精。 再次,技能的不断精进是古代工匠实现自我价值与通达人生境界的途径。一方面,与机器工业时代相比,手工业时代的技术发展与革新是缓慢的,然而,正是在这漫长的时间中,工匠得以将自己的理想信念、价值目标乃至人生感悟倾注于技艺与作品之中,从而达到道技合一的境界。庖丁从初解牛时所见只有牛,到三年后可以对牛的全身构造了如指掌,再到为梁惠王解牛时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达到了身心合一,无所束缚的状态。庖丁向梁惠王解释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②没有完全掌握牛的生理构造的厨师在解牛时难以避免会用刀割筋砍骨,导致刀刃受损,而庖丁之刀十九年解数千牛,其刃锐利如新,原因就在于他能够顺应牛的肌理,以“无厚入有间”,故游刃而有余。可见,庖丁追求的不仅是解牛技能的熟练,更是以解牛之技通达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道。另一方面,古代工匠提高技能的目的不仅局限于对工具价值的追求,还在于通过技术彰显人道主义价值。墨家学派的成员大多出身于工匠群体,墨子本人精通多种手工艺,尤擅机械制造,但他却主张兼爱非攻,认为技艺的巧妙在于能够为人所服务,“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③。 综上,从掌握应用技能时的创造性思维,到对技能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再到将技能作为实现自我价值与人生理想的途径,技能始终是工匠的核心,亦是工匠精神的核心。手工业时代的个体工匠以熟练精妙的技能为人所知,其所彰显的求新、求精、求道的精神也成为工匠们所追求的职业品质。
二、工匠精神塑造群体价值规范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工匠总体上属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统治者很少能够有意识地保存和传承关于技术的知识,技能和知识的积累实际上依赖于工匠共同体内部的传承。工业革命以后,人类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传统手工业日渐式微,传统工匠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在流水线上劳作的工人、从事设计的工程师以及企业家等。尽管手工业制造走向衰落,但源自传统手工业的工匠精神作为工匠共同体的智慧结晶以职业伦理的形式得以延续下来,极大地推动了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生产力进步,甚而成为其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城市中,劳动者可以凭借单一的技能为生,成为复杂社会机器中的一部分。专门化分工促进了具有共同信仰、共同职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罗马帝国时期就出现了城市手工业者组建的社团组织。然而,由于罗马帝国灭亡,希腊罗马时代的城市文化也随之消散,直至中世纪晚期,人口的增加与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工匠再次涌向城市以满足自身的需求。行业公会便在这一时期产生,Craftsman在14世纪最初指的就是“手工业行会的成员”,行会是同行业成员为了行业利益而结成的联合组织,手工业行会的职责包括保护工匠免受不公正待遇,协调生产,制定各类手艺的技术标准并为学徒提供相应的培训等。在行会中,从业人员按各自身份可分为学徒、工匠和师傅,其中师傅可以按照规定招收若干学徒,在学艺期间,师傅需对学徒严格要求,不仅要教授学徒相应的技艺,还要负责对其进行道德教育。在传艺的过程中,严谨、细致、勤奋、专注等职业伦理规范也在无形中得以传承,学徒需与师傅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学习结束必须制作出一件高质量的作品才可以晋升为工匠。 行业公会的兴起与发展表明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11世纪以前,工匠属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基本没有社会地位,但由于基督教教会接受了本尼迪克特派的主张,体力劳动被视为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劳动即是祈祷”①。熙笃会广泛吸收工匠,允许他们参加祈祷和宗教课程,这在事实上提高了社会下层工匠们的社会地位。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马丁·路德提倡“因信称义”,主张个人通过信仰可直接与上帝沟通,所有基督徒人人平等,在用德语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他以Beru(f职业、职务)同时翻译“上帝召唤”和“世俗职业”这两个术语,将神圣的召唤与普通人的工作联系起来,提出了蕴涵宗教伦理的天职观。②天职观将履行世俗劳动的责任看作个人道德活动的最高形式,每种正当的天职在上帝看来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与圣经中将劳动视为对人类偷吃禁果的处罚不同,新教主张个人的天职是履行其在现世中所处位置所赋予他的义务,这亦是上帝唯一认可的生活方式。天职观一方面极大地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劳动观念,使人们认识到工作只有分工不同,而无高低之别——一个人只要能够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能得到上帝的垂怜;另一方面为手工业者的工作注入了精神力量,使工匠劳动与宗教信仰产生了联系。自此以后,人们在价值层面的共识便是固守本职、精益求精,将自己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就是完成至高的道德义务。由此,行业公会的发展保证了工匠精神在工匠共同体内部的持续传承,新教天职观的传播则在社会范围内改变了工匠的社会地位,推动了工匠精神以职业伦理的形式在全社会发扬光大。 工匠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机器生产的大规模应用又进一步促进工匠精神深入人心,并且以职业伦理的形式在社会范围内泛化。以德国为例,作为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德国在英法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之时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直至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由于在技术和人才上基础薄弱,早期德国制造以仿制、冒充英法制造的产品为主,将大量粗制滥造的产品向英法等国倾销,这败坏了其制造业的声誉。1876年德国机械工程专家弗朗茨·勒洛在美国世博会上对德国制造的劣质产品进行了猛烈批评,引起德国国内的巨大震动。1887年,英国政府在修改《商标法》时要求来自德国的产品必须注明“德国制造”,其目的在于区分产品优劣,引导消费者抵制德国劣质品。基于此,德国企业意识到市场竞争不仅要有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德国政府也积极发挥作用,制定关税保护新生产业,修订鼓励出口的铁路运输费率,资助发展技术教育,着手培养众多企业家以发展工业。①从此以后,虽然德国制造业的主流是中小企业——约占德国经济贡献率的99.6%,占德国企业总数的92%。②这些中小企业多以生产制造单一产品的家庭企业为主,但是德国工匠秉持严谨专注、精益求精、品质至上的理念,坚持将单一产品做到极致,为产品注入了极高的单位产值。到19世纪末,西门子、拜耳等中小企业一跃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制造业品牌企业,德国制造也一改往日粗制滥造的恶劣形象,在化工与电力等行业远远超过英国,位居欧洲乃至世界之首,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工匠精神的泛化促使严谨专注、精益求精、品质至上成为德国社会各行各业人员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进而融入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中。20世纪以来,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种种动荡与变革,德国制造业历久弥新,其严谨认真与专注细致的工匠精神造就了德国产品安全、耐用、可靠的口碑,逐渐成为德意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日本。日本制造素以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而闻名,其工匠精神传统源自古代中国,在佛教与神道文化影响下产生的“神业”观念从内在层面驱使工匠对待工作倍加专注。近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工匠地位逐渐提高,工匠精神的影响也不再局限于手工业,而是泛化、扩延至各行各业,在日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匠精神产生长远深刻的影响。 综上,手工业时代的工匠精神强调微观层面的个人建构,机器工业时代的工匠精神则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建构。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模式使工匠从独异性的技术展现中脱离,现代意义上的服务于生产效率的技术工人由此产生,在传统工匠向技术工人转变的过程中,对技能的神性崇拜被与工业化大生产的目的需求相匹配的技能需求所取代。工业化社会对高技能工人的素质要求已经从对单一技能的熟练转变为对技术进步与机器革新的契合,由此,这一时期的工匠精神核心虽然依旧是技能,但侧重点已经由工匠的个人品质转向工人的自我约束,即职业伦理。西欧国家的职业伦理主要脱胎于新教伦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伦理逐渐褪去宗教的外衣,成为广义的工匠精神,其核心理念包括认真勤奋、努力刻苦等价值导向和追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展开,工匠精神进一步泛化为一种社会普遍价值观,其范围不再局限于技术工人,而是内化为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工匠精神捍卫人类主体价值 从手工业时代独特的个人品质到机器工业时代普遍化的职业伦理,工匠精神内涵的演化与技术发展(特别是制造方式的革新)的关联越来越紧密。由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推动物理、生物和数字系统的融合,也给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在从传统工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变的过程中,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日益提升,进而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过程的精准控制加强了对产品品质的保障;另一方面,制造过程中人力参与逐步减少,技术工人面临着被机器人所取代的风险。从制造活动的终端看,机器生产尽可能地减少了人为的意外因素,故而能够实现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由此,当机器的智能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从而实现生产的自动化时,传统意义上对产品品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不再适用于生产,毕竟制造活动的主体已经由人变为机器。在无时无刻不在与技术打交道的当下,技术的超前发展愈加远离人类中心,形成对人的离异与反控,因此,智能时代的工匠精神超越了个体品质和职业伦理的维度。 手工制造的产品大多满足一时一地的实际需求,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风格,是对物质世界的诗意创造,①充分表达了制造者的个体性;机器生产在控制生产过程和保障产品品质方面具有人类手工制造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是在标准化量产之中却暗含了同质化的力量。一方面,传统工匠手工制造的效率与机器生产的高效率无法相比,机器批量化生产取代了传统手工制造方式,大量具有相同标准的产品消弭了手工产品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强调科学与理性,重视将自然科学发现应用于技术进步,而忽视了蕴含在传统手工制造过程中的艺术价值和人文素养,在工匠向技术工人转变的过程中,个人的差异性被群体的同质性所取代。在电力与内燃机的驱动下,时空的阻隔被打破,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伴随着信息论和数字计算的革命性突破,技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方式,隐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同质化已经蔓延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首先是物质产品的同质化,当某种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时,符合同一标准的产品即被大批量地生产,与此同时,其他产品为了竞争市场份额也会采取相同或相似的设计进行模仿和量产。其次是文化产品的同质化,主要表现为在产品定位、设计、内容以及传播手段等方面趋于同一,例如各类选秀、真人秀等电视综艺节目。最后是人类交际的同质化,一项针对中国网民群体的调查显示,当前中国的网络公共舆论已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①,数字化的互联网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起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与他者擦身而过,在网络世界中寻找志同道合者,导致人们的视野日渐狭窄且趋于同一,进而加深了人类交际的同质化。同质化的持续扩散引发了智能社会下人类的生存危机。在各种同质化产品的包围中,人们看似接收着海量的信息与数据,实质上却并未获得任何新知识,感知本身呈现出一种“狂看”的形式,即“毫无节制的呆视”。②呆视意味着空虚,无论是物质产品抑或文化产品,人们所触之物看似花样百出,实则基本相同。在同质化的往复循环之中,人们的创新活力将逐渐丧失,最终沦为“单向度的人”。机器生产造成的同质化现象在工业革命时代就已被人们发觉,19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兴起的“工艺美术运动”曾主张通过弘扬传统手工制作的技艺之美与人文风格,以寻求在追求效率的批量标准化生产中突围。③面对随着现代技术发展而逐步加深的同质化危机,我们既无法阻挡技术发展的潮流,亦不可能完全放弃对技术的使用,想要逃离同质化的桎梏,必须要在智能时代重塑工匠精神的内涵与价值。 海德格尔在论及现代技术“集置”本质的危险时,曾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④,由技术引发的同质化危机,其救渡之路亦暗含于技术之中。斯蒂格勒在分析人的本质与技术的本质时指出,人是一种缺陷性存在,由于爱比米修斯的遗忘,人类没有获得专属于自身的本质,而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的火与技艺则是对过失的替代。技术于人而言本来是外在的,现在却构成了它所面对的存在本身,即人的存在是在自身之外的存在,也就是技术性的存在,人通过技术与外在世界打交道。前工业时代的工匠持有工具掌握技术,而现在,机器代替人成为工具的持有者,人不再是技术个体,人或者是为机器生产而服务,或者成为机器组合中的一部分。①就好比流水线上的技术工人,虽然参与了生产过程,但自身却并不掌握技能,进而丧失了生产制造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因此,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在智能时代弘扬工匠精神必须坚持以技能为核心,从工人的自我约束转向工匠的自我实现,在技术实践过程中突出人的核心地位。 亚里士多德曾言一切技术都以善为目的②,人类因存在意义上的缺陷而获得了技术,作为代具的技术之善表现为在源初之处为人打开了生存与行动的空间,使人拥有了本质而得以存在。可见,技术的代具性与人类的缺陷性紧密相连。希腊神话中的匠神赫菲斯托斯心灵手巧,精于制造,但却相貌丑陋,天生残疾;与之相反,宙斯为了惩罚人类获得火种,创造了名为潘多拉的完美少女,这个少女打开了瓮罐,诸神的礼物从中飞出,却给人类带来了苦难与不幸。天生残疾的赫菲斯托斯暗示着“缺陷之善”,即通过技术补足自身以实现目的;天生完美的潘多拉则是对“完美之恶”的隐喻,机器生产便宛如潘多拉魔盒,与手工制造相比,机器制造在生产效率和品质控制方面堪称完美,但也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危机与挑战。因此,面对不可逆转的技术智能化发展趋势,在智能时代弘扬工匠精神,必须处理好“缺陷之善”与“完美之恶”间的关系,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唤起被现代技术破坏的蕴含于手工制作中的风格气质与精神品质,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技术设计、使用等各个阶段促使技术向善发展。 技术不仅规定了人的存在方式,也构成了人类的进化方式。斯蒂格勒指出,技术的进化就是人类外在化的进化形式,人类的文化传承以技术为条件,换言之,技术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而蕴含在制造活动中的工匠精神则构成了人类发展的精神驱动力。手工时代的匠人在精神层面并不空虚,工匠在漫长时间中专注于掌握和提高技能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精神生活。工业时代的人与技术关系发生了变化,一味追求效率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工人在精神层面的匮乏与空虚,进而引发了同质化危机。当下,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时代向智能时代进发的关键时期,不仅需要技术层面的革新与进化,同样需要与之相协调的精神驱动力。未来智能社会的工匠精神要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仅仅是在生产过程中将人作为核心,更重要的是在与技术相对的整体性意义上捍卫人类主体性,而这恰恰是智能时代工匠精神的价值所在。
四、如何弘扬工匠精神的价值维度 从生产层面看,智能制造就是在机器生产的各个环节大量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以使机器生产趋向于智能化,换言之,就是通过机器的智能化部分地甚至全部取代生产过程中人的脑力劳动。机器的发展于人而言是向外的发展,为了适应机器运行的需要,人将自身的技能让渡给机器,只留下操作机器所必需的一小部分。因此,在生产制造层面弘扬工匠精神,核心就是恢复人在制造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将关注的焦点置于人的发展问题,促进人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自我完善。从微观层面看,技能是工匠的核心,工匠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对技能的掌握与深入,技能的提升始终是个体工匠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然路径。弘扬工匠精神必须重视工匠的技能提升过程,使其适应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①在工作中着重培养工匠精益求精、细致严谨、认真钻研的品格,鼓励和培养匠人的创新性思维,注重加强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关联,将产品作为内蕴自身品格的作品,而非简单的商品,推动匠人不仅成为机器的操作工,更重要的是做技能的传承者。从中观层面看,技能的传承关系到技能人才的培养问题,作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企业的良序发展离不开高技能人才,尤其是在技术创新、生产研发、转型升级等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重要阶段,高技能人才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企业建立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体系,提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方式,优化高技能人才使用机制,拓宽高技能人才晋升发展通道,将工匠精神的培育纳入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建设中,发挥高技能人才的模范引领和先锋带头作用。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当前正处于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时期,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解决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② 从生活层面看,快速发展的智能化技术不仅改变了制造模式,也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下的人们仿佛生活在技术之茧中,从生老病死到日常交往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技术的参与。技术的无处不在进一步导致了生产的泛化,即人们不只是在生产实践或工作中进行制造活动,同时是塑造自己生活的工匠,在此意义上,工匠精神亦是一种生活态度。对人而言,最初的技术是以生活为中心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劳动,也很少是以生产为中心或者以力量为中心的,③与其他动物相比,早期人类最为独特的优势在于具有符号创造、社会组织以及审美设计等能力,这些能力促使人们能够制造更为精巧的工具,使其满足生活的需要。人的身体具有不确定性,缺少如动物一般的某种先天本质,不确定性表明人的身体具有开放性,能够充分利用技术代具以获得稳定性,而这不能仅凭某一种技术得以实现,以生活为中心的技术必然是多元化的。因此,面向生活世界,弘扬工匠精神应当以技术的生活本质为基点。一方面,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文化演进的速度,弥合二者间的断裂与离异就必须将技术的发展方向重新置于人类的生活领域之中,技术的设计与制造应当围绕人类生活的切实需要而展开。另一方面,以机械为中心的单一技术的不断扩张将迫使人类进行分工,分工事实上肢解了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使人们只专注于单一的固定工作,生活质量的提高让步于技术权力的扩张。在生活中弘扬工匠精神,就是要促使人在面对技术的包围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特性,避免被技术所同质化,将支离破碎的人格与人性重新统一于多样性的生活之中,构造蕴含着人类理想生活样式的新精神文明形态。① 从生存层面看,技术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在发明技术的同时被技术所发明,作为技术性的存在,人通过技术与外在世界打交道。在智能时代保护和捍卫人类主体性就是要为机器之芯再加上一颗人类之心,即突出工匠精神的伦理维度,一方面是作为规范性的伦理守则,另一方面是与人类生存相关的伦理境遇。就前者而言,规范性具有双重指向,一是指生产活动中工人所遵守的职业伦理与制度约束,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人加以外部强制性的控制,从而确保生产制造的稳定性;二是指对技术的道德化嵌入,由于智能化机器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因此需要在设计阶段尽可能地将伦理道德嵌入机器的运行程序中,避免其在使用过程中造成危害。对于后者而言,与传统技术相比,智能化技术的他者性更为凸显,即作为独立于人的存在物与人所照面,进而引发了人们关于未来生存境遇的思考,如人工智能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取代人类。面对如此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考察人与技术的伦理关系,不仅是对规范性的讨论,更应将伦理关系作为人与技术的原初关系加以思考。面向历史,技术为人之生存打开了行动的空间;面向未来,技术亦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手段与目的。弘扬工匠精神,就是要在未来智能制造的过程中体现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气质,恢复和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进而实现人与技术的共在共生。
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8期